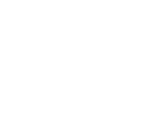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共识
如果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会理解它。这就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斯坦根对生活世界之间脱节的看法。我们两个物种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的根本不同,以至于这种差异没有什么意义。即使语言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依然存在。

今天,人们讨论的是机器的内部生活。专业技术被赋予了语言能力——这在以前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这些发展目前在学术界以外的地方成为头条新闻,在学术界,人工智能哲学的老问题被带到了前台:机器能有意识或意识吗? 这个命题激发了想象力,并引发了对深层存在主义和伦理奥秘的思考。
如果我们看过去的嗡嗡声和感觉的困惑,这里有另一个令人兴奋的讨论。它以重新表述维特根斯坦关于狮子的表述开始:如果机器会说话,我们会理解它吗?或者更确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可以与我们交谈的机器,在我们不同的生存模式之间可以有什么形式的理解呢?当然,理清这一点,就开启了共同理解的整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实践和概念两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它太多的思考,我们每天都这样做,不是作为爱好哲学家,而仅仅是作为积极的社会人。
根据一个学派的观点,我们的理解是通过我们在相互作用中提供给对方的回应不断显示出来的。我们在回复中展示了我们是如何理解对方的。一进入一个很热的房间,我可能会说这样的话,“这里暖和吗?”我的评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或接近或远离我的意图。有些人可能会把它当成征求意见,而其他人可能会用温度计读数来回答。然而,即使我对温度的抱怨被格式化为一个问题,它也可以被视为对某件事情的请求,其中适当的响应是行为,不是口头回复。如果你打开窗户,就像我们在北欧国家仍然做的那样,调节温度,我的感觉会是你理解我。那么,你的行动是我唯一需要的证据,作为我们共同理解的保证。我不需要偷看你的脑壳就知道你已经理解了我,因为只有大脑。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的共同理解是在这些转瞬即逝的互动时刻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我们一起穿越时间,一个接一个的行动,它不断地被创造、丢失和再创造。
根据这种说法,计算机有时会表现出我们对其他社会人所期望的互动理解形式。适当管理的机器响应可以给我相同的连接感、相似的观点和共享的理解,就像我与人类同胞一样。这种互动可以是实用的、治疗性的或快乐的。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对我们有意义。
那么,这能解决问题吗?我是说计算机能理解我们吗?不完全是。还有另一个学派从普通的语言哲学中表达观点。
当我们部署我们的概念时,这些概念通常局限于某些类型的主题。虽然音乐录音听起来很像管弦乐队,但我们绝不会想到谈论这种录音的音乐技巧。没有诗歌的许可,我们不会以那种扭曲的方式使用语言。技能是为生物保留的一种属性形式;它根本不适用于无生命的物体。同样,这一论点也与智力或思维有关。因此,“思维机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修饰法。艾伦·图灵(Alan Turing)反对这一保留意见,并认为历史语言偏见不应蒙蔽我们。我们过去没有观察到的事实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永远不会面对它。
机器人和会说话的机器之间的界限混淆了过去简单的区分。然而,对我们想要归因的代理类型的概念检查仍然是重要的。当我们试图理解对方时,对我们相互作用的伙伴进行分类是评估我们处境的一个有价值的方法。对方是谁,他们的年龄,认知能力,动机和兴趣,以及我们从事的活动,都是有意义的潜在资源。将一个不知名的人归类为骗子或警察会极大地影响我理解他们试图交流的任何东西的能力。如果我接受或忽略了这个人的邀请,不考虑这些信息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要传达的信息是,意义不仅仅包含在所传达的话语中;它还必须依赖上下文信息。
那么,在与机器交互时,如何处理这些顾虑呢?像LaMDA这样的东西的合适分类是什么,GPT-3或者下一个拐角处的什么东西?这是我们都在努力的地方。有些人拒绝接受这些系统仅仅是在硅芯片上执行的代码。因此,共同理解这个终极问题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分崩离析。其他人,不可否认地更少,接受延伸存在感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感觉的证据就在眼前。关于死亡恐惧的表达应该受到尊重,即使它们来自一台机器。如果骗子表现得很友好,我又有什么资格拒绝他们的友谊呢?